第二十一屆滇池文學(xué)獎(jiǎng)揭曉
經(jīng)過(guò)一系列按評(píng)獎(jiǎng)規(guī)則所進(jìn)行的評(píng)審,2025年第二十一屆滇池文學(xué)獎(jiǎng)于近日揭曉。浙江作家周如鋼的小說(shuō)作品《桃花源記》獲得年度最佳小說(shuō)獎(jiǎng);湖南作家劉威的散文作品《子彈飛往何處》獲得年度最佳散文獎(jiǎng);云南詩(shī)人徐建江(少莫)的組詩(shī)作品《秋天的素食主義者》獲得年度最佳詩(shī)歌獎(jiǎng)。年度大獎(jiǎng)空缺。
第21屆滇池文學(xué)獎(jiǎng)年度小說(shuō)《桃花源記》
授獎(jiǎng)辭:小說(shuō)《桃花源記》在“桃花源”的典故上做出現(xiàn)代的改寫(xiě),“源”既是初處,也是終地,但唯獨(dú)不可避世。世上有萬(wàn)千事,如萬(wàn)千朵桃花,一朵開(kāi),一朵敗,四十九個(gè)枝丫全全領(lǐng)受,方得新生。陶遠(yuǎn)明一覺(jué)醒來(lái),還有很遠(yuǎn)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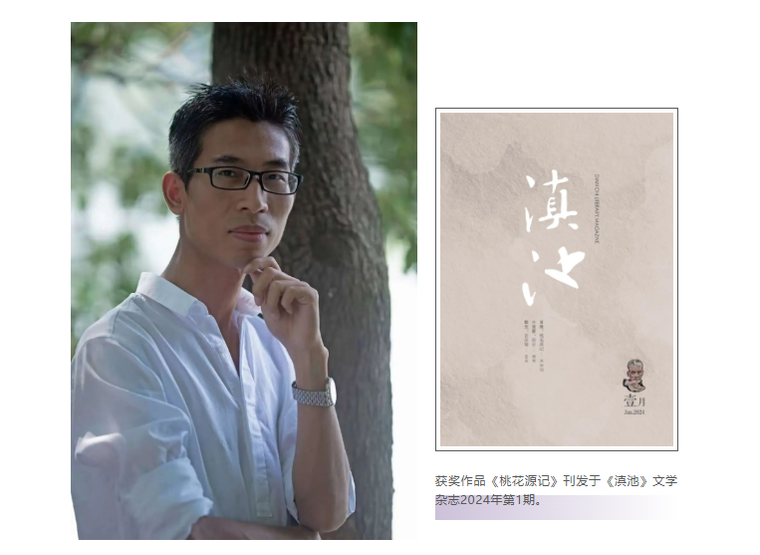
周如鋼,浙江諸暨人,中國(guó)作協(xié)會(huì)員。做過(guò)木雕織過(guò)布,擺過(guò)地?cái)偨踢^(guò)書(shū),當(dāng)過(guò)媒體記者編輯與主編。迄今已在《人民文學(xué)》《十月》等文學(xué)期刊發(fā)表小說(shuō)百余萬(wàn)字,部分作品被《小說(shuō)選刊》《小說(shuō)月報(bào)》《新華文摘》《長(zhǎng)江文藝·好小說(shuō)》等選刊選載及入選年度選本,著有中短篇小說(shuō)集《陡峭》《情緒發(fā)泄館》等,獲《莽原》文學(xué)獎(jiǎng)、梁斌小說(shuō)獎(jiǎng)、大觀(guān)文學(xué)獎(jiǎng)、浙江省新荷計(jì)劃·潛力作家獎(jiǎng)等。
答辭:我把小說(shuō)里的桃花源,設(shè)定在了人人向往卻只有少數(shù)人能進(jìn)入的世界,我也希望那個(gè)世界是一片凈土。但世上又哪來(lái)的凈土,若真有凈土,一定也是殘存在少數(shù)人的靈魂里。所以,一開(kāi)始,我想寫(xiě)一個(gè)人人向往的桃花源是被過(guò)度包裝的桃花源,是一片在現(xiàn)實(shí)廢墟里被高高架起的五光十色的桃花源,后來(lái),我覺(jué)得我們走過(guò)萬(wàn)險(xiǎn)千難,蹚過(guò)冰山雪雨,終究是需要一些溫暖的。于是,思來(lái)想去,我讓源子活成了表面有私心實(shí)則懷有大愛(ài)的人,讓陶遠(yuǎn)明成了一個(gè)有才華卻被命運(yùn)擠壓得支離破碎的人,我不再奢求這個(gè)陶遠(yuǎn)明與那個(gè)陶淵明能完成直接的對(duì)接了。小說(shuō)里的陶遠(yuǎn)明經(jīng)歷了高考被人頂替,有著優(yōu)異的成績(jī)卻只能淪為工地上的牛馬。小說(shuō)里的源子,為了陶遠(yuǎn)明的沖動(dòng)情緒而買(mǎi)單,莫名進(jìn)入了一般人進(jìn)不了的桃花源。而在這片人人向往的,可以選擇如何投胎換世的桃花源,最終仍然被他所棄,他又一次完成了生命能量的傳遞。時(shí)代的車(chē)輪滾滾向前,多數(shù)時(shí)候,我們普通的小人物只是被車(chē)輪碾過(guò)的小碎末罷了,但我仍然希望我們?cè)谄D難前行中能夠懷抱一絲善良和溫暖,這樣便能多一份希望。或許,互相取暖才能證明人間的值得。要感謝《滇池》的厚愛(ài)和包容。給這個(gè)粗拙的小說(shuō)一些溫暖。
第21屆滇池文學(xué)獎(jiǎng)年度散文《子彈飛往何處》
授獎(jiǎng)辭:體校射擊隊(duì)的槍膛中,始終存放有少女時(shí)代待發(fā)的榮耀子彈和豐實(shí)的專(zhuān)業(yè)細(xì)節(jié)。當(dāng)屬文之手摳動(dòng)追憶的扳機(jī),子彈在誠(chéng)善幽微的心靈、摯切簡(jiǎn)約的語(yǔ)言、克制澹然的敘述、徐疾有致的節(jié)奏中飛行,受享靶場(chǎng)饋贈(zèng)的陣痛與蛻變,最終精準(zhǔn)洞穿了青春靶心背后當(dāng)下生活的來(lái)路和真義。劉威書(shū)寫(xiě)自己獨(dú)異的生命彈道,是對(duì)個(gè)人史的回眸載錄,更是對(duì)心靈史的深度究問(wèn)、共相萃取,以此鼓舞讀者勇毅飛抵命運(yùn)子彈射往的未來(lái)他方。

劉威,湖南長(zhǎng)沙人,青年作家,高等教育學(xué)碩士。中短篇小說(shuō)、散文發(fā)于《清明》《青年文學(xué)》《上海文學(xué)》《綠洲》《滇池》《青年作家》等刊,有作品被《中篇小說(shuō)選刊》《散文海外版》《散文選刊》轉(zhuǎn)載并收入各種年選。出版中短篇小說(shuō)集《塞上書(shū)》。獲第五屆三毛散文獎(jiǎng)。
答辭:感謝《滇池》,感謝評(píng)委。是的,我曾是體校生。《子彈飛往何處》寫(xiě)的就是13歲那年在體校的一些事。那年小學(xué)畢業(yè),初一開(kāi)學(xué)就被選進(jìn)了市里剛成立的射擊隊(duì)。學(xué)習(xí)訓(xùn)練,集體生活,比賽拿獎(jiǎng)。小口徑手槍?zhuān)p筒獵槍?zhuān)棥B?tīng)著很有意思,但小小年紀(jì)需要獨(dú)自往來(lái)兩座城市間走讀,里頭藏著很多艱辛。2023年夏天,一杯穆塞萊斯喝下去,和一位好朋友很自然地聊起了這段經(jīng)歷的另一面,當(dāng)然沒(méi)有事無(wú)巨細(xì),但我發(fā)現(xiàn)我能夠說(shuō)出來(lái)了。再后來(lái)我將那段經(jīng)歷寫(xiě)下來(lái),投給了《滇池》,就是后來(lái)發(fā)出的《子彈飛往何處》。另一面依舊隱晦,是多舛的年少,是需要擁抱時(shí)舉目無(wú)親的迷惘和恐懼,這些只能交給以后。今夏,我聽(tīng)說(shuō)了許多草原的故事,其中有個(gè)細(xì)節(jié)特別有趣。哈薩克族牧人家里通常養(yǎng)幾百頭羊,為了不和鄰居家的羊弄混,會(huì)給自家羊的耳朵打上專(zhuān)門(mén)的標(biāo)記,從最原始的拉一道口子到后來(lái)的打金屬扣。轉(zhuǎn)場(chǎng)的奔波會(huì)造成羊耳一部分潰爛脫落,牧人拾到斷耳,會(huì)埋進(jìn)草場(chǎng)的泥土中,以腐肉喂養(yǎng)螞蟻。我猜這“螞蟻”除了螞蟻,也包含土壤中的一切微小生物。聽(tīng)出了“鯨落萬(wàn)物生”的宏大,內(nèi)心震蕩許久。在騰沖的司莫拉佤族村,我曾和一個(gè)用自家房子開(kāi)店的大姐聊了很久。我買(mǎi)她店里的涼薯,她請(qǐng)我喝她自釀的百香果汁,不要錢(qián),只要“不嫌棄邋遢”。我從沒(méi)吃過(guò)那么野的果子,也從沒(méi)對(duì)陌生人那樣敞開(kāi)過(guò)心扉。因?yàn)闊o(wú)須再見(jiàn)的傾聽(tīng)者,講述似乎平添了勇氣。人生沒(méi)有回頭路可走,無(wú)可否認(rèn),和槍支打交道近十年,有許多旁人難及的體驗(yàn),但一些經(jīng)歷也是我曾嘗試擺脫的陰影。不過(guò)后來(lái)我發(fā)現(xiàn),快樂(lè)地過(guò)活,要學(xué)會(huì)揀選。而有勇氣記錄的時(shí)候,要及時(shí)記錄。一些人,一些事,和許多個(gè)瞬間,促成了文字的生發(fā)。感謝每個(gè)愿意讓我的文字被看見(jiàn)的人,感謝那些愿意給我擁抱的人。
第21屆滇池文學(xué)獎(jiǎng)年度詩(shī)歌《秋天的素食主義者》
授獎(jiǎng)辭 :《秋天的素食主義者》是一組關(guān)乎“空間詩(shī)學(xué)”和“語(yǔ)言移栽術(shù)”的充滿(mǎn)詩(shī)意哲思和具象生活質(zhì)感的詩(shī)歌,一個(gè)深居簡(jiǎn)出的詩(shī)人,深諳哲學(xué)、邏輯學(xué)和語(yǔ)言學(xué)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在日復(fù)一日煉金術(shù)般的錘煉過(guò)程中,以時(shí)間的載體、記憶的重構(gòu)、空間的轉(zhuǎn)接直抵語(yǔ)言和詩(shī)性的本質(zhì)。這是一組關(guān)于“語(yǔ)詞行動(dòng)”和“在時(shí)間中如何存在”的深度詩(shī)篇。詩(shī)人借深刻的哲思和沉靜的語(yǔ)言,在記憶的廢墟和語(yǔ)言的困境中,進(jìn)行著艱難而有效的“生命紡織”,試圖在時(shí)間的流動(dòng)中確認(rèn)自身和記憶的無(wú)縫“拼貼”,并留下那縷“可以上升的桂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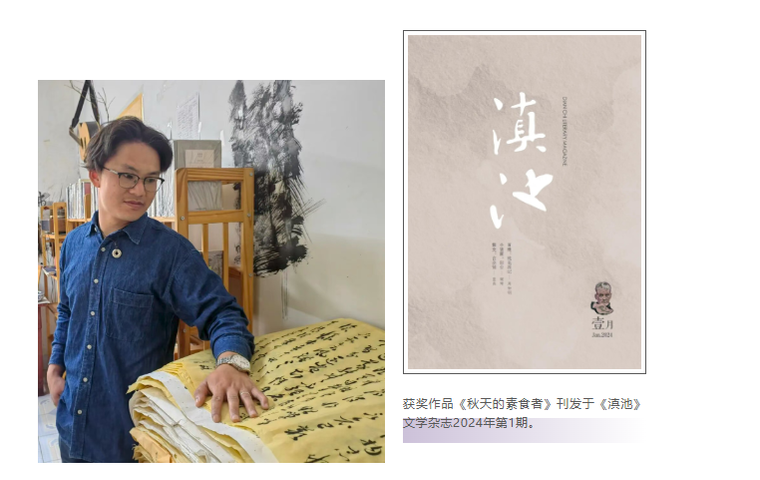
徐建江(少莫),1992年生于云南省丘北縣,2017年畢業(yè)于海南師范大學(xué)數(shù)學(xué)系。詩(shī)人,自由書(shū)法家,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從事書(shū)法培訓(xùn)教育。2009年起開(kāi)始寫(xiě)詩(shī)。出于練習(xí),每星期堅(jiān)持寫(xiě)三首詩(shī)。
答辭 :謝謝!謝謝《滇池》雜志社、評(píng)委會(huì)!首先一段流水的敘述或許是必要的:2009年,我曾遭遇了一場(chǎng)嚴(yán)重的意外事故,在醫(yī)院里經(jīng)歷了搶救、開(kāi)顱手術(shù)。在那以后的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我曾深刻地、幾乎絕望地體驗(yàn)著生命巨大的虛空感。在那段康復(fù)的時(shí)間里,我嘗試去寫(xiě)東西,嘗試通過(guò)文字去和時(shí)間撕扯著。然后是十余年的,西西弗斯式的閱讀與創(chuàng)作。還有我的父母——我知道這么說(shuō)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是殘忍的,我深深地知道——那次意外后,他們對(duì)我所體驗(yàn)到的那種失而復(fù)得的感覺(jué),讓他們努力地包容我的偏執(zhí)。正是在與自我的靜謐的相處過(guò)程中,我不斷地、從未放棄過(guò)去建構(gòu)自我的和諧。近年來(lái)我時(shí)常詢(xún)問(wèn)自己這個(gè)問(wèn)題:“在這十余載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中,你是否已經(jīng)慢慢地找到了內(nèi)心的寧?kù)o、達(dá)至內(nèi)心的和諧?你是否已經(jīng)看清了精神中隱匿的創(chuàng)傷,破解了那些涌現(xiàn)的形象,并慢慢讓它們靜息下來(lái)?”在日復(fù)一日的創(chuàng)作中,我漸漸意識(shí)到一個(gè)問(wèn)題:我想是時(shí)候該認(rèn)真地思考一下,該如何確立自己的寫(xiě)作風(fēng)格了。即我應(yīng)該怎樣在自我之同一性的概念下,去理解并實(shí)現(xiàn)母語(yǔ)之個(gè)性化的可能。即我必須面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我所熟識(shí)的母語(yǔ),將以什么樣的開(kāi)場(chǎng),引入我同樣熟識(shí)的自我之對(duì)世界的體驗(yàn)。這個(gè)開(kāi)場(chǎng)的個(gè)性化,規(guī)定了諸在場(chǎng)者之于自我的母語(yǔ)中忽然現(xiàn)身的樣態(tài),甚至規(guī)定了它們上到手頭時(shí)的樣態(tài)——體驗(yàn)的特征。這里又關(guān)涉到一個(gè)有關(guān)創(chuàng)作的深刻的母題,即母語(yǔ)。寫(xiě)詩(shī)不僅僅是一種個(gè)體性的表達(dá),不僅僅是抒情。它更應(yīng)該是一個(gè)詩(shī)人對(duì)于其自身所處的整個(gè)文學(xué)傳統(tǒng)的體驗(yàn)與反思,是詩(shī)人對(duì)于其母語(yǔ)及其自身的命運(yùn)的感知。詩(shī)人對(duì)于語(yǔ)言之傳統(tǒng)、命運(yùn)的感知與共鳴,應(yīng)該是貫穿于其創(chuàng)作過(guò)程的一種現(xiàn)時(shí)性的領(lǐng)悟。這種領(lǐng)悟能讓詩(shī)人體驗(yàn)到——其母語(yǔ)的命運(yùn)正在流經(jīng)他,并且正在塑造詩(shī)人自身的命運(yùn)。一個(gè)詩(shī)人應(yīng)該能夠深刻地感受到其母語(yǔ)的處境,并且明白這也正是他自身的處境。然后在這種感知能力下,一個(gè)詩(shī)人還應(yīng)該逐漸意識(shí)到自我之心理的任務(wù):對(duì)于自我心理、精神的諸現(xiàn)象的明晰的判斷與認(rèn)知。這種對(duì)自我的認(rèn)知,能讓一個(gè)詩(shī)人依據(jù)自身持有的獨(dú)特的敏感性,對(duì)某一等待對(duì)談的語(yǔ)言場(chǎng)景展開(kāi)創(chuàng)造,以實(shí)現(xiàn)母語(yǔ)的個(gè)性化表達(dá)。我始終在思考這些問(wèn)題:經(jīng)驗(yàn)、直覺(jué)、情感、隱喻、震驚、語(yǔ)詞、意象等等。但我很清楚:在真正的靈感到來(lái)以前,我所寫(xiě)的一切都不過(guò)是平庸之作。生動(dòng)形象,是文學(xué)作品的第一原則。而能夠生動(dòng)形象地去把握住人類(lèi)關(guān)于自我的最高理想,則是文學(xué)作品能實(shí)現(xiàn)的最高形式。因此就目前來(lái)說(shuō),我所寫(xiě)出來(lái)的詩(shī)都是失敗的。我始終記得那個(gè)情景:16年前,當(dāng)我在醫(yī)院里昏迷了16天后醒來(lái)。我問(wèn)母親:“媽媽我在哪里?”她朝我微語(yǔ):“你在醫(yī)院里啊,你不記得了嗎?”那是我第一次深深刻刻地感受到——所有的一切恍如一場(chǎng)夢(mèng)。如今的一切也仿佛是一場(chǎng)夢(mèng):我正在慢慢地、一點(diǎn)點(diǎn)地變成一個(gè)詩(shī)人,在這里和大家分享著我的體驗(yàn)與詩(shī)。最后,我要感謝我摯愛(ài)的妻子:謝謝你對(duì)我的貧窮與偏執(zhí)的包容,我愛(ài)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