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滄桑的“70后”青春之歌—— 作家段玉芝長篇小說《鳥耘圖》研討會舉辦
《鳥耘圖》,一部關(guān)于耕耘、成長與奮斗的長篇小說。小說以女主人公朱雀華從農(nóng)村到城市的事業(yè)奮斗為主線,情感經(jīng)歷為輔線,呈現(xiàn)了從20世紀(jì)90年代起長達(dá)20年的時間跨度里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由此折射出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進(jìn)步。

8月23日上午,由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小說創(chuàng)作委員會和濟(jì)南市作家協(xié)會聯(lián)合主辦、濟(jì)南出版社協(xié)辦的長篇小說《鳥耘圖》研討會在濟(jì)南舉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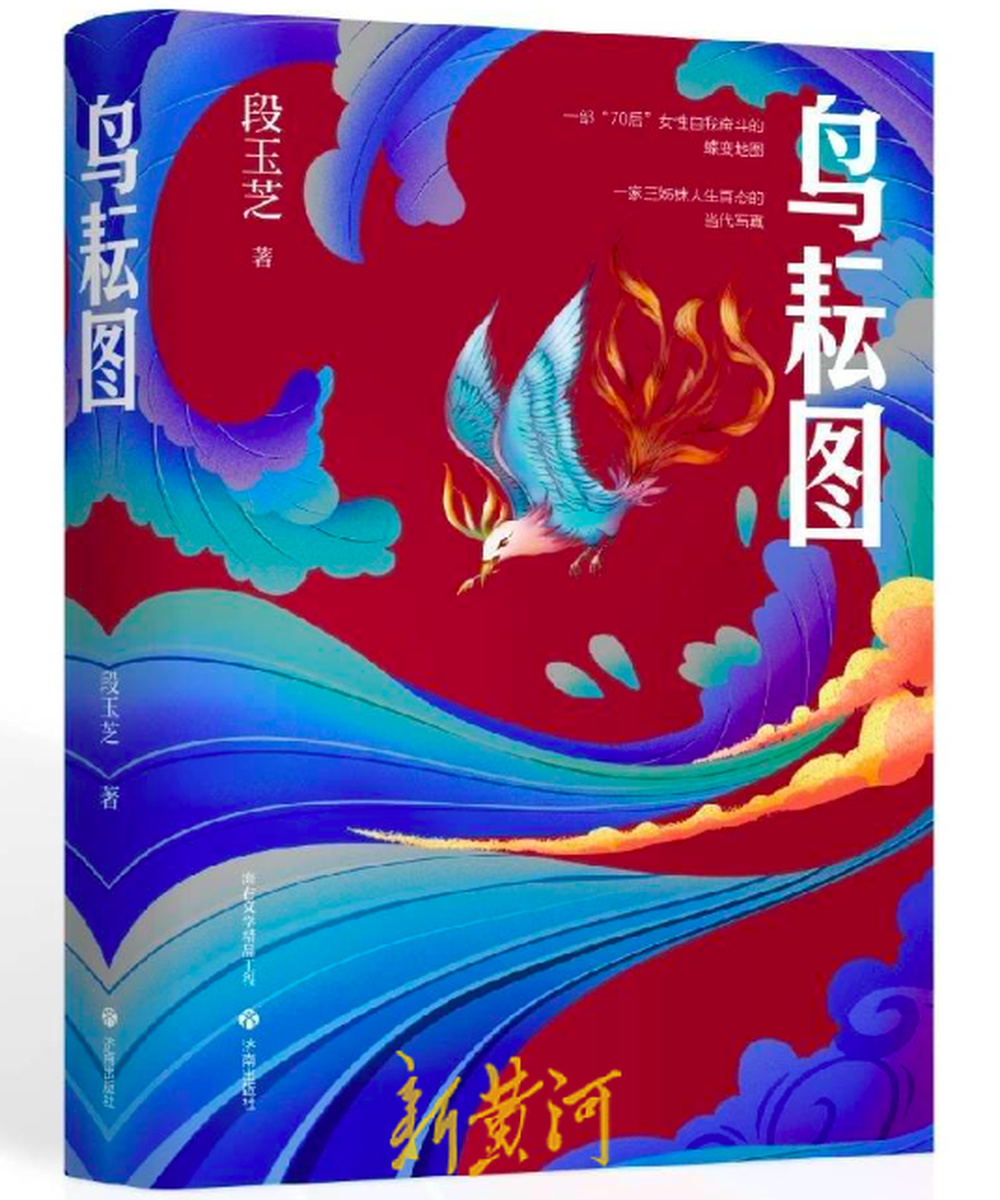
《鳥耘圖》是山東省作協(xié)重點(diǎn)扶持作品,同時入選濟(jì)南市“海右文學(xué)”精品工程第三批扶持項目。《鳥耘圖》的作者段玉芝,是山東省作協(xié)第五批、第六批簽約作家,在全國文學(xué)期刊發(fā)表小說作品100余萬字,曾獲第五屆“泰山文藝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獎)。
山東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新收獲
當(dāng)日的研討會由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山東文學(xué)》主編劉玉棟主持,濟(jì)南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張鴻福,濟(jì)南出版社高管、海右文學(xué)精品工程出版統(tǒng)籌李建議,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陳文東分別致辭。
劉玉棟在主持詞中指出,《鳥耘圖》這部作品,試圖通過個人經(jīng)歷透視社會發(fā)展,通過社會發(fā)展映照個人的奮斗與命運(yùn),同時弘揚(yáng)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大舜精神。
張鴻福在致辭中介紹了“海右文學(xué)”精品工程及取得的成績,并從鮮明的時代特征、突出的濟(jì)南特色、堅韌的成長歷程和紛紜的人物形象四個方面對《鳥耘圖》進(jìn)行了剖析。
李建議在致辭中表示,作為這本書的編輯,他至今清晰記得第一次通讀全稿時的情景,“讀到一些感人細(xì)節(jié)時,淚眼蒙眬,桌子上的稿件也變得模糊。后來與同事們討論稿件,常常會突然陷入沉默,抬頭時才發(fā)現(xiàn)彼此眼里都含著淚水。當(dāng)我們?yōu)橹烊溉A的堅韌落淚時,是在為所有不向命運(yùn)低頭的人鼓掌。”
陳文東在致辭中表示,《鳥耘圖》是段玉芝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對于她個人來說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這部作品也是山東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個新收獲。并對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大舜的“耕耘”精神給予高度肯定,認(rèn)為這些精神是山東人生命的底色,也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
有著光亮底色的“70后”代際書寫
在主題研討環(huán)節(jié),莫言研究專家、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賀立華,著名作家、《當(dāng)代小說》原主編劉照如,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院常務(wù)副院長、教授馬兵,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山東省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會長叢新強(qiáng),山東師范大學(xué)教授、《百家評論》副主編趙月斌,山東師范大學(xué)教授顧廣梅、陳夫龍,濟(jì)南市作協(xié)副主席常芳,濟(jì)南市作協(xié)副主席、《當(dāng)代小說》副主編王玉玨,著名編劇、作家、制片人高克芳等對《鳥耘圖》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賀立華認(rèn)為《鳥耘圖》是一曲滄桑的“70后”青春之歌。他認(rèn)為,小說真實再現(xiàn)了“70后”一代的生活樣態(tài),此外,“小說以去技巧化的敘事,質(zhì)樸、鮮活的語言,傳達(dá)了深刻的人生啟迪,給人溫暖和力量,給人光明和希望。”同時賀立華也希望,段玉芝在今后的創(chuàng)作中向更高的藝術(shù)境界躍遷,要始終有一個“高飛遠(yuǎn)舉”的東西。
劉照如表示,讀《鳥耘圖》最讓他震動的,是“雀華的理想不斷破滅,卻能不斷修正目標(biāo),為了責(zé)任堅韌地向前”,“其實很多人因為現(xiàn)實生活和責(zé)任,活出了自己不喜歡的樣子。但是雀華不是,她能夠接受改變后的自己。”
馬兵表示,《鳥耘圖》作為“70后”的代際書寫,有三個特點(diǎn):“一是寫常態(tài)的人和常態(tài)的人生,現(xiàn)在很多小說寫的都是幽暗的、偏執(zhí)的甚至抑郁的人生,《鳥耘圖》卻有光亮的底色;二是對個人記憶的珍視,小說里的主人公有鮮明的個人記憶時間線,拒絕被群體記憶淹沒;三是有很多細(xì)節(jié)讓人難忘,這些細(xì)節(jié)讓人物的形象更加立體飽滿。”
叢新強(qiáng)從“《鳥耘圖》的人與時代及其精神”對作品進(jìn)行了解讀。他認(rèn)為,這是一部“70后”的“回望”之作、“記憶”之作、“還原”之作。“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既有個人化的經(jīng)歷,也寫出了“70后”一代人共通的人生歷程。這部書還提供了真實的時代氛圍,那是個很有活力的時代。人之所以能堅持走下去,精神支撐是必不可少的。”
趙月斌認(rèn)為這部書可以看作是作者的精神自傳,也可以看作是“70后”這一代人的精神自傳。從小說中可以看到大時代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向上向善的精神特征。不他也提醒作者在尚善的基礎(chǔ)上,“不妨讓主人公更多地直面生活中的殘酷事件,以增加一些對人性多面性的探索”。
顧廣梅從女性成長敘事角度來解讀作品,認(rèn)為《鳥耘圖》有著獨(dú)特的氣質(zhì),飽含著生命的激情,不矯情,不造作,“70后”的成長有它的特殊性,“他們更相信知識改變命運(yùn),更相信個人奮斗,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他們面臨物質(zhì)性和精神性的雙重困擾。但主人公朱雀華因為確信有一種時代的精神是上揚(yáng)的,確信奮斗可以讓生命更精彩,所以特別有一種主體性的精神力量”。
陳夫龍把《鳥耘圖》置于段玉芝的創(chuàng)作軌跡中加以審視,認(rèn)為這部長篇的創(chuàng)作,是她多年從事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之后的一種突圍。他認(rèn)為段玉芝心懷暖玉,擅長發(fā)掘人性的善,“朱雀華對家庭、父母、弟妹、同學(xué)、朋友之愛,令人感動”。
常芳認(rèn)為這部書同時呈現(xiàn)了個體之光與時代之光,“命運(yùn)曾經(jīng)給了雀華姐弟最致命的打擊,但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時代背景之下,他們有了前所未有的機(jī)遇。作為個體,他們吃苦耐勞,堅韌不拔,各有所成,因而自帶光芒。這些個體的人的光芒,匯聚成了一個時代的亮光”。
王玉玨認(rèn)為《鳥耘圖》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一是“容易看”,作者除了有作家立場、作家坐標(biāo),還有讀者立場、讀者坐標(biāo);二是精彩,文學(xué)性強(qiáng),主題好,可以說是一部女版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70后”版的《平凡的世界》,“它努力呈現(xiàn)的是主人公人性和生命底色當(dāng)中最美好的那些部分,這些都屬于文學(xué)書寫中恒久的主題”。
高克芳說,作為“70后”,她在書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認(rèn)為這部書具有很強(qiáng)的改編電視劇的底蘊(yùn)和特質(zhì),“首先《鳥耘圖》的時代背景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目前好像還沒有一部電視劇是反映這個時間跨度的;然后是人物的性格鮮明,人物的命運(yùn)跌宕起伏;此外,故事的展開和節(jié)奏也很符合電視劇,情節(jié)的飽和度特別高。”
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yùn)的精神是相通的
研討會上,《鳥耘圖》作者段玉芝也分享了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歷程。她表示,最初產(chǎn)生寫《鳥耘圖》這個想法,是在七八年以前,“那時候我先后參加了大學(xué)、中學(xué)同學(xué)的聚會,也跟大學(xué)時同宿舍的好友深入聊了聊。看到每個人不同的境況,過著不同的生活,我很有感觸,就有了寫一寫70后這一代人的想法。一開始想寫群像,比如一個宿舍六個人的生活狀態(tài)。后來覺得群像不夠集中,就把目標(biāo)鎖定在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雀華身上,中間也附帶了她宿舍幾個人的狀況。其實雀華身上有好幾個人的影子。當(dāng)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想到雀華,就想起《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孫少安和孫少平,最后我才明白,原來他們的奮斗精神、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yùn)的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有了大體構(gòu)思和框架,當(dāng)時的題目是《雀華》。”
在長時間的構(gòu)思和運(yùn)量過程中,段玉芝意識到,不能單純地寫個人的成長,要與時代緊密結(jié)合起來,“這期間我爬千佛山,再次到大舜石圖園,看到象耘鳥耘的傳說的時候,突然覺得雀華的精神其實是有淵源的,于是我就看大舜的傳記,研究大舜精神和大舜文化。看完之后,我就把小說的題目改為《鳥耘圖》,與中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結(jié)合起來。”
研討會最后,段玉芝對各位專家、學(xué)者提出的寶貴意見表示了感謝,“希望能在今后的創(chuàng)作中不斷突破自我,寫出更有深度和廣度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