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大地上雕刻 時間為之倒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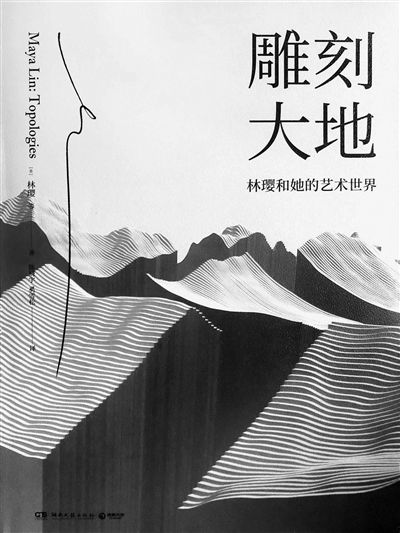
《雕刻大地:林瓔和她的藝術(shù)世界》一書,是享譽世界的華裔建筑師林瓔的集大成回顧,收錄了林瓔30年來的50個作品、8個系列、300幅圖片,以及十余位世界頂級藝術(shù)評論家、策展人,比如邁克爾·布蘭森、菲利普·朱迪狄奧等人對林瓔及其作品的評論文章。
林瓔的成名作是1982年11月13日落成的《越戰(zhàn)陣亡將士紀念碑》。1980年,林瓔從1441幅入圍作品的海選中脫穎而出。她當(dāng)時21歲,是耶魯大學(xué)的本科生。兩面拋光黑色花崗石墻體組成V形碑體,在1959年~1975年陣亡的58183名越戰(zhàn)美國士兵的姓名將按照時間順序鐫刻在墻體上,在柔和的莫奈式背景色里,地表仿佛切開了一道黑色的傷口。林瓔希望,人們沿著這道“傷口”緩步之時,每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是否能堅強地接受這些死亡。
這幅設(shè)計圖與公眾習(xí)慣的紀念碑截然不同,顯得過于抽象。林瓔的年紀、種族和身份引發(fā)質(zhì)疑,反對的聲浪迅速猛烈。有些老兵團體想要在碑體的頂部加上寫實的士兵雕像,而林瓔極力維護最初的設(shè)計概念,認為添加的外來物徒增笨重,會破壞設(shè)計原初的意味。后來,聽證會達成了妥協(xié),林瓔的方案最終通過,士兵雕像也建成了,與紀念碑隔開了一段距離。
林瓔對紀念碑的興趣集中于這個時代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從越戰(zhàn)、民權(quán)運動到女性權(quán)利、北美原住民問題,以及至今仍然延續(xù)的無限的《什么正在消失?》的項目。
落成于1989年的《公民權(quán)利紀念碑》,圓形桌面上順時針刻著一條模仿日晷的民權(quán)運動時間線,從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開始,到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刺殺事件結(jié)束,民權(quán)運動的時間線和運動中被害的40位公民交織在一起,水流柔緩地拂過這些字跡,金的名句刻在帶有弧度的水墻上:“我們現(xiàn)在并不滿足,我們將來也不會滿足,除非正義和公正猶如江海之波濤,洶涌澎湃,滾滾而來。”
落成于1993年的《女性之桌》,石頭的湖藍色是耶魯大學(xué)的顏色,橢圓的桌面上刻著一個數(shù)字組成的漩渦,記錄著耶魯每年的入學(xué)女生人數(shù),從最初一連串的0、0、0,直到個位數(shù)、十位數(shù)、百位數(shù)、千位數(shù),螺旋從水源處開始,越來越寬,把開放性留給未來。
《什么正在消失?》并非實在建筑物,而是一種去物質(zhì)化形式的實驗探索,利用網(wǎng)站和電子技術(shù)展現(xiàn)地球的生態(tài)歷史,整個過程自我生成,人們可以通過點擊了解這些歷史,每一個在線探索這段生態(tài)歷史的人,都受邀貢獻一段他們的個人記憶。該項目不僅強調(diào)我們在失去什么,同時展示實踐的具體行動,以新型宏觀途徑構(gòu)想我們和我們星球的不同結(jié)果。
建筑與其他藝術(shù)很大的不同點在于,它通常是配合場所主題進行的創(chuàng)作,藝術(shù)家需要對特定場景作出回應(yīng)。場景和建筑不僅是記憶的承載工具,還是情感的擴大器,通過意象、表征和環(huán)境氛圍勾起并增強人們自身的情感。紀念碑需要借助符號的指向性來保證死者的在場,紀念的內(nèi)容通過大眾的主動參與得到定型,使紀念碑獲得神圣地位的氣氛需要借助生者身臨的反應(yīng)得到實現(xiàn),構(gòu)成一個事件的集合,個人的記憶匯流成為集體的記憶。
林瓔曾說,她設(shè)計越戰(zhàn)紀念碑的原因之一是“讓100年后的孩子來到這里,對戰(zhàn)爭的高昂代價有清醒的認識”。相比直白刻板的士兵雕像,林瓔的越戰(zhàn)紀念碑更能喚起人們對時間深度和連續(xù)性的感知,這是帶有史詩性聯(lián)想的建筑敘事。當(dāng)一個人帶著沉思的自由站在那里時,那個人也成為了越戰(zhàn)紀念碑的一部分,也成為了我們記憶中歷史的一部分。
評論家達娃·索貝爾說:“盡管時間只朝著一個方向流動,林瓔卻再一次讓時間為她倒流。”
除了上面提及的這些紀念碑,它還在瑞典瓦訥斯《11分鐘》隆起的地面上來回游走;在安阿伯密歇根大學(xué)的《波場》、邁阿密聯(lián)邦法院的《顫振》和紐約芒廷維爾《風(fēng)暴國王波場》里周期性波動;在《西經(jīng)74度》《東經(jīng)106度》和《紐約緯度》等作品里,時間與空間重新組合;紐約賓夕法尼亞車站中央走廊屋頂上的《時蝕》(1995),是真正以人類的維度講述時間;《什么正在消失?》的宗旨就是“扭轉(zhuǎn)時間”,要讓我們記住事物原本的樣子,通過回憶,讓我們對所處的環(huán)境更加敏感。
林瓔作品使用的媒介很廣泛,除了傳統(tǒng)的石頭、青銅或黏土,還有一些工業(yè)材料鐵、鋼、玻璃、賽璐珞等,她經(jīng)常使用的還有大頭針。《車站河》《針河:長江》《科羅拉多河》等作品,一枚枚大頭針如同楔入的節(jié)點,綿展蜿蜒,帶來“逝者如斯夫”的體悟。
從藝術(shù)意圖的角度來看,自然與人造物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是大地藝術(shù)品的基本特征。林瓔的環(huán)境作品具有大氣且簡潔的風(fēng)格。林瓔對藝術(shù)熱愛的同時包含了對數(shù)學(xué)和科學(xué)的強烈興趣,她認為建筑是這些興趣有力的結(jié)合體,她憑借本能的直覺創(chuàng)作,不過,所有的直覺都建立在對力學(xué)、物理、地貌等實際的研究與觀察之上,絕非向壁虛構(gòu),而是萬物歸一的美感。
保羅·戈德伯格說她有“省略的勇氣”。還有比切入地面的V形花崗巖墻體更簡單的形式嗎?林瓔能讓看上去簡單明白的姿態(tài)傳達深刻的復(fù)雜性和模糊性,而且,她的作品是對形式與組合的探索,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情境中,用林瓔的話說,“是這個世界的存在”。
在21歲,籍籍無名之時,林瓔就清晰地理解這一點。從那時開始,她就以創(chuàng)作呼喚自我,建筑的自我。一種沉思性的、探索自身存在,也能引發(fā)人們主動探索自我的藝術(shù)。
林瓔有個簡單愿望,她想讓人們意識到他們周圍的一切,而這不僅是物質(zhì)上的環(huán)境,也包括了人們的心理世界。雕塑周圍的空間是可以被感知的,而不是空無一物,在那里,有一個氣場,人們可以感覺到。林瓔的所有作品,都要召喚人們進入建筑的內(nèi)部,不僅在于可見的物質(zhì)形體,更在于跨越時空的心靈的交匯,去感受一種隱藏的自然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