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科幻小說能拯救地球嗎?
近來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引起了很多年輕人的共鳴,它著眼于全球環境問題的惡果,同時也讓年輕一代們參與其中,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出謀劃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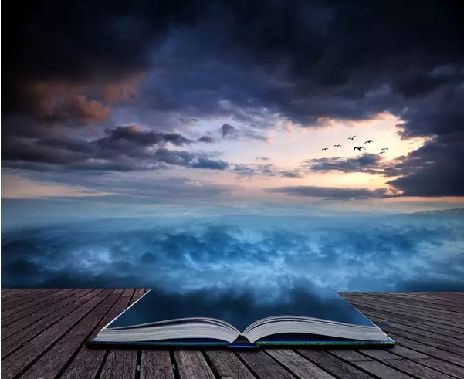
美國西南地區因干旱而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在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因各自占有的科羅拉多河份額日益減少而爭論不休之時,一旁的加州卻虎視眈眈,想將其全部據為己有。在這個“滴水貴如金,同盟逝如沙”的時代,荒漠里的唯一真理就是:想喝水,先流血。
上述有關美國西部大旱災的說法或許略顯夸張——就目前而言,這種設想還只是虛構的。這是作家保羅·巴斯加盧比(Paolo Bacigalupi)作品《水刃》(The Water Knife)的前導宣傳語。如今,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小說風頭正勁,這本書也是其中的新作之一。這類體裁的作品常稱為“氣候科幻”(climate fiction, cli-fi ),簡而言之,就是探討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極端后果。
其實此類概念也并非新鮮事物。19世紀80年代,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在他一些小說中就嘗試過這類概念,但人為因素造成氣候變化的主題直到進入20世紀才開始出現在文學作品中。20世紀60年代,英國作家J.G.巴拉德(J.G. Ballard)開創了世界末日主題的文學創造風潮,比如小說《神秘來風》(The Wind from Nowhere)。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提高,此類主題的小說人氣也越來越旺,如今在購物網站亞馬遜上搜索“氣候科幻”,有1300多條結果。
步入千禧年之后,氣候科幻已由原來科幻小說的分支發展為自成一派的文學體裁。和以往的科幻文學不同,該體裁的故事很少關注人們虛構的科技,或是天邊遙遠的行星。它重點關注的是地球,審視各類污染、海平面上升、全球變暖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這類文學體裁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學課程里,在科技與人文學科和行動主義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讓年輕讀者們更容易接受環保話題——由此可見,在各種應對全球變暖問題的舉措中,文學發揮的作用超乎人們的想象。
現在,氣候主題的電視電影在大小熒幕上都漸漸興起,這對于吸引年輕人的興趣大有幫助。2014年,克里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史詩巨制《星際穿越》(Interstellar)中,美國中西部變成了沙塵暴地區,前途堪憂,人類只好尋找新的星球定居。電影《雪國列車》(Snowpiercer)里,人們阻止全球變暖的實驗失敗,導致人類重新進入了冰河紀。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大受歡迎的氣候小說三部曲《瘋狂的亞當》(MaddAddam)正由HBO電視臺改編拍為電視劇,而該頻道另一部人氣頗高的電視劇《權力的游戲》(Game of Thrones)也有意無意地觸及了全球變暖的主題。
作家兼環境活動家丹·布魯姆(Dan Bloom)在2007年左右創造了“cli-fi”(氣候科幻)這個詞,希望能借此將冗長乏味的“climate fiction”(氣候科幻)變得更有吸引力。布魯姆說道:“我從沒定義過,也沒想過要去定義一種新文學體裁。”在他看來,他只是想造個朗朗上口的流行語,以提高全球變暖問題的關注度。這項策略很成功,布魯姆稱,2012年,阿特伍德在Twitter上用了這個詞,將其介紹給她的50多萬粉絲。此后,“氣候科幻”一詞慢慢站住了腳跟,出版社和書評人也開始將其視為一種新的文學種類。
從這一方面來看,“氣候科幻”的確是一種當代文學現象——誕生之初為一種(通過模仿而傳播的)文化迷因,而現在則借助社交媒體的力量成長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如今,Twitter上關于氣候科幻小說的標簽用得很頻繁,好讀(Goodreads)上有讀者創建的書單,而Facebook上也有一些小組,其中一個小組就專門推薦適合年輕人閱讀的氣候科幻小說。
想想當代“氣候科幻”的起源,我們便不會對其在高中和大學讀者群中漸長的人氣感到驚訝。在2015年2月《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專欄中,“氣候科幻”作家薩拉·霍丁(Sarah Holding)撰文稱,此類文學體裁“將年輕讀者和他們身邊的環境重新聯系起來,讓他們看清其中的價值。尤其在當今社會,年輕人把大量時間都浪費在虛擬世界。”
環境主題的小說與當今青少年文學里的反烏托邦潮流相輔相成。巴斯加盧比的2013年小說《溺水的城市》(The Drowned Cities)和2011年小說《拆船人》(Ship Breaker)向我們展示了海平面上升是如何改變美國地形的,而薩拉·科洛珊(Sarah Crossan)的2012年作品《呼吸》(Breathe)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一個由穹頂覆蓋的城市里,因為那時的氧氣,已經是稀有品了。
此類文學作品帶來的并非只有逃離現實的刺激,它已經成為鼓勵年輕人進入科研領域的跳板。多年來,在美國學界,學生對STEM課程(科學,技術,建筑,數學)的興趣逐年下減。2012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的結果顯示,美國學生在科學方面的能力表現排名僅為第20名(共34個國家參與)。但目前,從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到劍橋大學繼續教育學院(Cambridge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海內外的許多大學都開設了“氣候科幻小說”的相關課程。2015年早些時候,來自霍利奧克大學(Holyoke)的幾位學生,為研究巴斯加盧比的獲獎小說《發條女孩》(The Windup Girl)中的基因工程概念,提取出了草莓的DNA。在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氣候科幻”課程的學生就經常用他們的班級博客來分享科學新聞,并在書評中引用各類科學文章。一位英語專業的學生在博客中坦言:“其實,面對大量的科技專業術語,我經常不知所云,感覺自己智商不夠用。”之后這個學生發布了一篇關于阿特伍德小說《洪災之年》(Year of the Flood)的書評,內容詳盡,探討氣候變化怎樣影響多個農業領域,并討論了其中涉及的化學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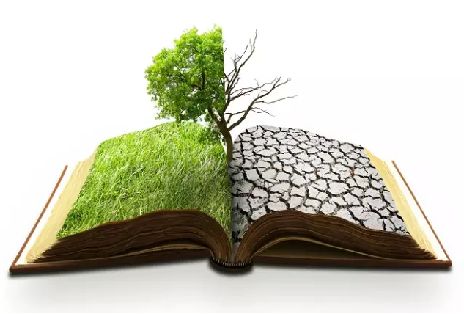
STEM課程使學生們望而生畏,然而科學與人文的交融卻能產生實效,鼓勵更多學生投入STEM領域的嚴肅研究。由文學和創意寫作輕松入門,《一次一個詞拯救地球》(Saving the World One Word at a Time)的作者艾倫·斯扎伯說道:“對于那些自以為對科學沒興趣的學生來說,科學也變得能夠理解了。”他曾提出一種觀點,“氣候科幻”類文學作品具有將環境問題私人化、去政治化的能力——少把氣候變化視作一個毫無人性的話題,反而能最終啟發人們實實在在的行動。泰德·豪威爾(Ted Howell)在天普大學教授“氣候科幻”課程,他稱,宣傳氣候變化的傳統方式對于他的學生已不再適用。“一旦他們對全球變暖的基本知識框架有了大致理解,便不想再研讀關于全球氣溫是上升2%還是4%的資料——他們想知道的是該如何應對。”豪威爾說道。
當然,也并非每個人都相信氣候科幻小說的潛力。2014年,氣候信息網的創始人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就曾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他擔心這類科幻小說只會加強人們根深蒂固的想法,而不能改變任何人的觀念。“不信氣候變化的人只會把這些故事當作證據,證明氣候變化是虛構的,作家們為了達到戲劇化效果而夸大其詞,”他說道,“已經相信氣候變化的人會被故事吸引,但那些夸張的末日故事套路又可能會使他們偏離氣候變化的議題,甚至于將問題物化。”
廷德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把氣候變化放入小說故事中,可能會減少讀者對現實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感,或是將之簡化為沒有現實補救措施的模糊概念。天普大學課堂里的學生表示,他們也有同樣的感受。“當我們意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真正有效措施需要涉及一系列生活方式上的實質性改變,并會因此在金錢、權利和影響力上有所犧牲時,我們就會感到泄氣。”豪威爾說道。雖然失望,但也并非毫無希望。他表示,這些不確定性也能幫助我們強調改革的巨大潛力。
而挑戰也在于此。“科學并不能告訴我們該怎么做,”金索沃爾在小說《逃逸》中寫道,“只能告訴我們它是什么。”故事本身并不是解決方案,但它們能激勵我們去行動,這也許就是氣候科幻小說的呼聲為什么在年輕讀者的心中這么有地位。作為明日的科學家和領導人,他們最有可能解決好前輩們未能完成的任務,解決好氣候變化問題。氣候科幻小說,與其背后的科學原理一樣,所呈現的前景似乎都是一片凄涼。但在這些駭人的預言中,還藏匿著希望,現在改轅易轍也還為時不晚。正如阿特伍德在《瘋狂的亞當》中所言,“人們需要這類故事,因為不管前途多么黑暗,有聲的黑夜總是好過無聲的空虛。”
原文選自:大西洋月刊
譯者:張驍 編輯:欽君


